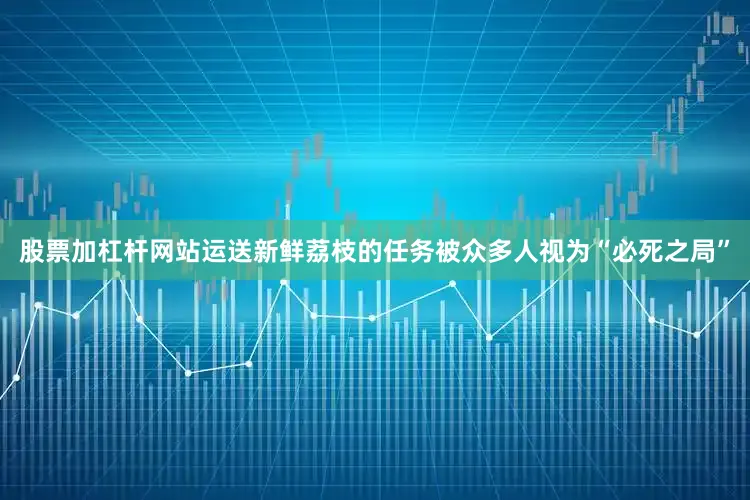毛泽东主席共有六位子嗣,其中岸英与岸青幸存,而岸龙及另外两位儿子不幸早逝,另有一位儿子(岸红)至今行踪未明。
1953年,毛泽东同志意外收到了贺子珍女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欣喜地告知:我儿毛毛(毛岸红)的下落已得确认。
此时此刻,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已英勇牺牲于朝鲜战场,而次子岸青则饱受重病之苦。
按常理推断,能够寻回毛毛无疑是件喜出望外的大喜事,然而,毛主席却最终未能认回这个失散了长达十九年的儿子。
究竟发生了何事?详情繁多,一言以蔽之:辛酸。

毛主席
毛毛身世之谜
1932年11月,毛主席与贺子珍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毛岸红。
此刻,正值毛主席政治生涯遭遇低谷之际,仅一个月前,他在宁都会议上遭受了指责,随之而来的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的剥夺。
为了关照母子二人,毛主席特意为岸红挑选了一位奶娘。
奶娘偏爱唤他“毛毛”,因此,“毛毛”便成为了毛岸红昵称的由来。
毛岸红的降生,为毛主席的生活注入了无尽的欢声笑语。
某日,毛主席戏谑地对尚不能言语的毛毛开起了玩笑:“我仅有‘毛’字一个,而你却拥有两个‘毛’,这看来是你的本事比我更胜一筹呢。”
然而,那段充满欢乐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当毛毛年仅三岁时,红军不得不告别苏区,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长征之旅。
鉴于毛毛年幼,毛主席与贺子珍不便携其一同随部队远征,无奈之下,毛主席只得将毛毛委托给坚守苏区进行游击战的毛泽覃照顾。
毛主席不得不将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中,这一决定虽显无奈,亦带有几分“残忍”,然而在当时,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鉴于毛泽覃乃毛主席之胞弟,而他的妻子又是贺子珍的嫡亲妹妹,将幼子托付予毛泽覃与贺怡之手,毛主席与贺子珍均感到无比安心与踏实。

贺子珍 贺怡
然而,随着中央红军的转移,苏区的斗争环境愈发严峻,危险程度远超往昔。
在自身安危尚无法确保之际,毛泽覃毅然将子女托付给了当地一位姓朱的农民。
毛泽覃并未向那位姓朱的乡亲透露毛毛的出身与来历,仅仅是轻描淡写地提及:“这孩子的父母双亲均为红军战士。”
乡邻们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毛毛,为了确保他的安危,这对夫妇特意为毛毛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朱道来。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于江西瑞金的一处山林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在英勇地掩护游击队员撤离的过程中,这位年仅29岁的革命先烈不幸英勇捐躯。
自此,毛毛的行踪变得扑朔迷离,即便是毛泽覃的妻子贺怡亦无从知晓其确切去向。
费尽周折终于觅得毛毛的踪影,不料却意外现身另一位母亲。
有人或许会问,毛泽覃英勇捐躯,那么他的妻子贺怡又去向何方了呢?
实则,当红军撤退出苏区之际,毛泽覃与贺怡领受着各自迥异的指令。
中央指令毛泽覃率领红军独立师奔赴闽赣边界的战场,而贺怡则被派遣至江西赣州开展秘密工作。
因此,在毛泽覃英勇就义之际,贺怡与毛泽覃并未同在一线。贺怡直至很久之后方才得知毛泽覃壮烈牺牲的消息,至于毛毛的行踪,她更是茫然无知。
此事此后始终萦绕在贺怡心头,如同一块难以消融的“心病”。对于毛毛,以及她的姐姐和姐夫,贺怡始终怀抱着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之情。
自建国伊始,贺怡便不遗余力地寻觅毛毛的踪迹,其间亦偶有所获,寻得些许线索。
数位战友向贺怡透露,他们在江西发现了一名孩子,其身世及外貌特征与毛毛极为相似。
闻悉此讯,贺怡欣喜若狂,遂于当晚驾车,从广州疾驰至江西。
遗憾的是,贺怡所乘坐的越野车在蜿蜒的山路途中遭遇不幸,事故导致贺怡遭受了严重的伤势,终因伤势过重而遗憾离世。
身为贺怡的亲姐姐,贺子珍陷入了无边的自责漩涡之中。
料理完妹妹的后事,贺子珍毅然决然地作出抉择——向组织寻求协助,以寻觅毛毛,此举亦是为了完成妹妹未竟的心愿。
1953年,贺子珍同志致信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的邵式平同志,恳请组织协助寻找其失散多年的女儿毛毛。
贺子珍未向毛主席告知此事,鉴于毛主席必定会反对她的这一举动。
贺怡在世时,曾向毛主席求助,恳请他向江西、福建等省份发出关照,协助寻找毛毛。
“如此长年累月,毛毛或许早已离世,亦或是被善心之人抚养成人。”
“往昔战乱频仍,抚养一个孩子实属不易。如今孩子已成人,国家亦步入和平,却要求将孩子归还,此等举措对于养育者而言,实乃极大的不公。”
为此事,贺怡曾与毛主席激烈争执。

毛主席与贺子珍在红军时期。
因此,贺子珍私下里请邵式平帮忙寻找毛毛,此事并未向毛主席透露。
鉴于对毛主席的崇高敬意,以及对一位母亲的深切理解和同情,邵式平迅速组建了一支工作团队,并指派江西省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同志全权负责此事。
起初,她选择革命圣地瑞金作为切入点,以此为基点,逐步向外围区域拓展搜索领域。
于瑞金之地,王家珍同志在瑞金县政府主持了一场尊崇老红军的座谈会。
众多老红军战士纷纷表示,他们皆知晓红军干部昔日于苏区安置子女的往事。然而,岁月蹉跎,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迫害,存活下来的红军后裔寥寥无几。
面对这一结果,王家珍虽已有所预料,然而老红军战士的话语仍旧令她深感失望,随即情绪低落,泪水夺眶而出。
王家珍心中默默立下誓言:纵使面临再大的挑战,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她必将不屈不挠地继续探寻。
座谈会的尾声过后,王家珍不辞辛劳地踏遍了瑞金县每一寸土地,逐户走访,细致询问,甚至查阅了《瑞金县志》的典籍,却依旧未能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正当王家珍筹备启程,前往临县展开走访之际,叶坪乡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一位长者向王家珍讲述道:“昔年,红军曾在邻村驻足,有一位名叫朱盛苔的村民,他曾经收留了一名红军遗孤。”
那位老者接着言道:“朱盛苔提及,那孩子的父亲曾是红军中的高级将领。”
王珍家夜以继日地赶至叶坪乡,急切地寻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
一番简短的交谈后,王家珍便断定无疑:朱盛苔昔日确实曾收养了一名红军遗孤。
王家珍询问:“您是否清楚孩子的父亲名字?”
朱盛苔轻轻摇了摇头,回应道:“我仅知道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至于他的姓名,我并未向他询问,他亦未主动告知。”
王家珍问:“我想见朱道来,可以吗?”
王家珍闻言,瞬间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朱盛苔的话语透露出:“道来并未在家,上个月,南京有几位干部来访,他们将道来带往了南京。”

毛主席与贺子珍在红军时期。
朱月倩与贺子珍均称孩子之母。
朱盛苔透露,将朱道来引领至南京之人,名为朱月倩,此女乃昔日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霍步青的贤内助。
朱盛苔,王家珍好奇地询问:“她与朱道来有何关系,你为何愿意把你的孩子托付给她?”
朴实无华的朱盛苒回应道:“她自称是那事件的母亲,而且,她所述的内容与往事的细节完全吻合。”
“孩子的母亲已然到来,我怎能忍心阻隔他们母子的重逢?”朱盛苔语带哽咽,话语落定后,她黯然垂下了头颅。
显而易见,朱道来的离别使得他的养父心中充满不舍,然而,即便如此,朱盛苔这位宽厚而质朴的人,依旧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委屈自己,以成全他人”。
朱盛苔,王家珍好奇地询问:“你们家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保存得怎么样了?”
朱盛苔感慨道:“家境贫寒,我们从未给孩子留下过一张照片。”
朱盛苔的夫人黄月英回忆道:“我们保存着孩子的近期照片,而自南京之行归来后,道来曾特意寄回了一张。”
照片中的朱道来已长成一位青年,其眉目之间,依稀可见毛主席年轻时那独特的神韵。
然而,仅凭这一点,王家珍仍不敢断定照片中那位朱道来便是贺子珍长久寻觅的毛毛。
王家珍迅速向邵式平省长报告了此事,得到省长的鼎力支持后,她携带黄月英,即刻启程前往南京,并成功与朱道来及朱月倩会面。
在阐明了自己的来意之后,朱月倩便向王家珍娓娓道出了她过往的经历。
王家珍对朱月倩透露:“贺子珍同志同样在寻觅那些昔年失散的孩童,那些孩子的境遇与道来的情形相仿。”
王家珍言:“我欲携道赴上海一游,愿其与贺子珍同志相会,恳请您予以准许。”
朱月倩神色略显沉重,沉吟片刻,最终开口:“嗯,好吧,便让道前往上海一遭。我们同为母亲,我对贺子珍同志的这份情感,自然是能够感同身受。”
朱月倩屡次强调:“那孩子必定是我的儿子,这一点绝无虚假。”
于是,王家珍携朱道来与黄月英一同抵达上海,不久便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热切期盼中的贺子珍。
一见朱道来,贺子珍立刻泪如泉涌,她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从发顶到脚跟,再从脚跟望回发顶。
经过几番仔细端详,贺子珍坚定地开口道:“没错,是你,你就是我的毛毛。毛毛,这是你的乳名,而你正式的名字,则是毛岸红。”
此刻,黄月英从包裹中取出一件灰色的薄棉衣。
目睹这件薄薄的小棉袄,贺子珍顿时泪水如泉涌。这乃是由旧时灰布军装改制而成,忆及当年将毛毛交付毛泽覃之际,她将囊中所有银两尽数留下。
同时,鉴于对毛毛可能受寒的担忧,贺子珍便以毛主席的旧军装为材料,从自己与毛主席的棉衣中取出棉絮,不惜通宵达旦,为毛毛赶制了一件温暖的小棉袄。
岁月流转,那件小棉袄已然显得陈旧不堪,其间的针脚也略显笨拙,然而,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深深的母爱。
毛毛失而复得,这一喜讯令贺子珍既兴奋又喜悦,然而,历经风雨的贺子珍依旧保持着她的冷静与理智。
她深知,毛毛不仅是她的骨肉,也是她与毛主席的结晶,此事实终需告之毛主席,并赢得他的首肯。
关于朱道来是否为毛毛的疑问,同样牵动着另一个人——毛毛舅舅贺敏学的神经。
贺敏学亦强调,认亲一事举足轻重,切不可任由情感左右,更不宜仓促作出抉择。
在贺敏学的精心安排下,朱道来接受了医院的血液检测,检验结果迅速揭晓,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如出一辙。
此鉴定手段颇似传说中的“滴血验亲”,其精确度受限,所得结果的真实性亦存疑虑。然而,在当时,这无疑是速度最快、可靠性最高的方法。
目睹这一结果,贺子珍愈发坚信自己的推断:朱道来正是多年前失散的那位儿子毛毛。

贺子珍与贺敏学家庭合照
夺子风波
在获得毛主席的批准之后,王家珍携同朱道来,一同抵达北京,并入住中组部的招待所。
贺子珍亦为身处北京的千金李敏寄去一封挂号信,她在信中传递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并叮嘱李敏务必抽空去见一见那位她尚未谋面的亲哥哥。
接到母亲的信件后,李敏迫不及待地赶赴招待所。与朱道来相见,李敏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亲近之情,朱道来亦感同身受。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李敏携朱道游历了整个北京城。为了一路陪伴哥哥尽情享受美食、畅饮佳酿、畅游名胜,李敏几乎将身上的零花钱悉数耗尽。
“毛毛归来”,这一消息也传至了中央领导层的耳中。周总理与朱老总不辞辛劳,抽出时间前往招待所探望了朱道来。昔日曾在中央苏区共事的诸多同志,亦纷纷前来表达关切与问候。
众人皆言,朱道来的面容与年轻时毛主席的形象颇为相似。
在探望朱道来的途中,周总理特地吩咐工作人员为朱道来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影像。
冲洗完照片后,周总理便将此幅影像呈献给了毛主席。
周总理提问道:“你注意观察,这张照片中的孩子,长得有谁相似吗?”
毛主席反复端详,凝视良久,他感慨道:“这孩子与我弟弟毛泽覃年轻时模样颇为相似。”
鉴于众人都坚信朱道来便是毛主席失散已久的亲生之子,因此,朱道来最终选择留驻北京。

毛主席
接下来,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毛主席何时以及如何与毛毛实现重逢,这一环节完成,毛毛方可算真正踏入父亲温暖的怀抱。
事情突变。
原来,朱道来抵达北京后便决定留驻彼处。得知此讯的朱月倩,心急如焚,遂不顾手头一切事务,匆匆忙忙地赶往北京。
抵达中组部招待所后,朱月倩毫不犹豫地决定将朱道来带回南京。
招待所的同事们怎敢贸然应允她的请求?得知朱月倩同志曾是红军时代的老革命,他们一方面竭尽所能地安抚她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及时向中组部相关领导汇报了此处的情况。
面对前来了解情况的中组部领导,朱月倩坚定地表示:“朱道来就是我的亲生儿子,任何人也别想将他从我身边夺走。”
朱月倩断言:“无论对方是谁,若有人胆敢夺我之子,我必将与之对簿公堂!”
在情绪激动的驱使下,朱月倩语气坚决地威胁道:“若不将我的儿子归还于我,我必将在此地自行了结此生……”
至此,原本喜气洋洋的一大喜事竟演变成了一团糟的棘手问题。
怎么可能有一个儿子会有两位亲生母亲?朱道来的真实身世究竟又是如何?
为深入了解此事,中组部特地派遣人员至招待所主持了一场调查会议。该会议连续召开三天,贺子珍与朱月倩各持己见,一时间难以辨明真相。
贺子珍与朱月倩均坚定地声称:“朱道来便是昔日与我失散之子”,且他们各自拥有形形色色的证人或实物证据作为佐证。
然而,鉴于时间久远及诸多因素,朱月倩与贺子珍的叙述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及矛盾之处,或者说,其中存在瑕疵。
无独有偶,两位母亲均坚信“朱道来即我的亲生之子”,无论遭遇何种境况,她们都坚决不愿割舍对儿子的牵挂。
毛主席艰难抉择
鉴于案情错综复杂,最终,周总理向毛主席做了详细汇报。
毛主席会怎样判断此事?

年轻时的毛主席
在前文,我曾阐述过毛主席的立场,他并不打算寻找他那失散的儿子。
毛主席曾对贺怡感慨道:“孩子虽非亲生,但他人如同亲生父母般,倾注心血,历经艰辛,将孩子抚养成人,实属不易。”
毛主席曾言:“在我看来,养育父母之恩,实乃胜过生育之恩。”
于是,在周总理将这一棘手的挑战托付于毛主席之际,毛主席仅以一句简洁的话语回应:
“无论他是谁的子女,终究是革命事业的传承者。我想,不妨将他托付给人民和党组织。”
毛主席一锤定音,朱道来既未能重返毛主席(或贺子珍)的身旁,亦未能留在朱月倩的身边。
遵循周总理的指示,朱道来最终投奔至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同志麾下,并由帅孟奇同志亲自担纲,负责对其悉心照料与培养。
在接纳朱道来之前,帅孟奇同志已悉心抚养了众多烈士的后代,将朱道来交付给她照料,无疑是一个明智而合适的选择。
尽管贺子珍与朱月倩对毛主席所做出的抉择心中存有几分不悦,她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默默承受这一既定的事实。
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位历经风霜、饱尝人间百味的母亲间悄然形成了一种共识:她们不再纠结于谁是朱道来的亲生母亲,而是将他视如己出,亲如骨肉。
由此,朱道来便拥有了四位母亲:贺子珍的母亲、朱月倩的母亲、黄月英的母亲,以及帅孟奇的母亲。

朱道来
朱道来始终与那远在千里之外的三位母亲保持书信往来,以慰藉她们的忧虑。她们也时常寄来衣物与食物,以表关怀。
尽管在三位母亲中,黄月英的家境较为寒微,朱道来却时常能收到她寄来的礼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他幼年时尤为钟爱的美食。
据朱道来的同窗所述,在求学于中小学的岁月里,朱道来堪称全班最为富有的学子,每月所领的零花钱便高达八九十元。
在那个时代,80余元绝非一笔微不足道的金额,当时,即便是十八级干部的月薪,也仅此数额。
朱道来怎这么富?
理由显而易见,除了那位帅气的母亲定期给予的零花钱,贺子珍与朱月倩也几乎每月都会寄来一笔零用金。
尽管朱道来的养母家道贫寒,然而每逢佳节,她总会寄来象征吉祥的“压岁钱”。尽管金额有限,但这其中蕴含的深情厚谊,却胜过千金不易。
朱道来最终脱颖而出,考入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他被分配至一家国防科研机构工作。
令人惋惜的是,1971年,朱道来因疾病过早离世,当时年仅37岁。
结语
有人质疑,毛主席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亦无认领之情,此等举动未免显得过于冷漠。

毛主席
1937年,目睹贺子珍去意已决,毛主席深情地发表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话语:
我素来性情坚忍,泪水不轻易滑落眼眶,却也有三桩事,让我潸然泪下。
一是那贫瘠苦难百姓的哀嚎声令我无法承受,目睹他们遭受折磨,我忍不住泪如泉涌。
其次,那些曾跟随我的通讯员,我心中难舍他们离去。他们中的一些甚至英勇牺牲,每当想到此处,我便不禁泪流满面。
三者在贵州,听闻你遭受了伤势,生命岌岌可危,我不禁泪如泉涌。
毛主席在认子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这么“绝情”?
只有一个原因。
他不愿目睹骨肉分离的悲剧重演,同时亦深切体恤养父母的情感。
“道是无情却有情”,在毛主席的胸中,这“情”所指乃“大情”,而这“爱”所体现的,便是“大爱”之深!
汇融优配-手机配资软件-配资专业炒股配资门户-国内正规最好的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在线炒股配资其实每个人都在偷偷做小动作
- 下一篇:没有了